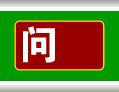邵伟华贴那张大字报的时候,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省市党政领导,对党中央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思想准备,对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不理解,视为反革命行动,就利用职权,调动西安各大国防工厂的民兵队伍,镇压红卫兵的造反行为。
邵伟华所在的军工厂临近郊区,复员军人多,青年工人也多。所以,工厂党委根据省委指示,组织了三千年青工人准备去市里镇压。他们在厂政治部赵书记的动员下,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形象与文革宣传画如出一辙:头戴柳条安全帽,双手紧攥铁锹把木棍。只待赵书记一声令下:“准备出发!”
邵伟华是厂里的优秀党员,当然也被党委挑选成为镇压红卫兵的“打手”。他听着听着,先是在忍。忍着忍着,没时间了!
只见他从队列中“唰”地一下站出来了:“赵书记,省委组织工人进城镇压大学生,违背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用武力,用打的办法对起来造反的学生是不可行的!我们今天进城打学生的人,个个都是年轻力壮的,你们想一想,那么年轻的学生,他们还是不懂事的孩子啊!我们一棒子打下去,怎么扛得住,打死怎么办?别人把你兄弟姐妹打死打伤了,你们怎么想?假如说学生是反革命,党中央毛主席会对学生做说服教育工作的。建议厂党委取消进城镇压大学生的决定。”
他转向大伙儿:“我们不能去,不能打学生!”
场内立刻有人响应了:“我们决不向大学生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参加民兵青年队的人顿觉惭愧,随即一致同意邵伟华的意见,继而散会,回家。
这下可好,邵伟华又捅了大篓子!
党委领导认为他煽动工人不服从领导,不支持党委决议,不是反革命行为是什么?但邵伟华说的又话有理有据。党委领导一时无法处理,只能暗地里给他记一笔黑账。
厂里的工人没有进城,可是其他厂共出动了上万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见学生就打,被打晕倒胳膊腿被打断的,头被打破全身是血的比比皆是,惨不忍睹。
这一下把学生们惹火了,他们像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青年一样,群情激奋,抬着受伤的学生到街上游行示威,还抬到省政府市政府门口,向领导示威抗议,要血债血偿,要伸张正义给说法,要交出打学生的幕后凶手!
这样的游行在市里进行了三天三夜。那些被惹怒的学生还跑到了各工厂里散发传单,学生们拿着血衣举着血淋淋的照片、满含热泪哭喊着:“工人老大哥,支持我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吧救救我们红卫兵吧!”
看着这悲惨的情景,邵伟华不由自主地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厂党委对学生来厂宣传,十分紧张,立即召开各车间党政负责人会议,说学生是反动的,他们手拿着血衣是在进行反革命煽动,是有意造假,是在煽动反革命情绪。让工人不要听,更不要进城支持。
邵伟华这个人天生爱打抱不平,看不惯省市领导组织工人打学生,更不满厂党委的定性。他想起毛主席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就准备去市里交通大学查个真假看个究竟。
厂里其他30多个同情学生的工人听说后纷纷表示愿意跟着他一同进城。这回,邵伟华自然而然地又成了带队的头。于是,他们步行30多里地,来到了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大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我国最早兴办的高等学府之一,其前身是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1921年改为交通大学。1956年国务院决定将交大内迁至西安,1959年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
邵伟华第一次踏进高等学府的大门,展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惊奇不已,四通八达的水泥马路旁,绿树成荫,掩映着一栋栋教学楼。花园内鸟语花香,各种花草争奇斗艳。就好像走进了天堂。
他心情很复杂,既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自己第一次走进高等学府,领略到了如此优越的校园环境;难受的是,自己小时候因为家穷,偷听别人讲课头被打烂;后来又因为家穷,弟妹多即使上了学,还是不得不辍学;还是因为家穷,穷到基础单薄知识不够用,必须用尽全力才能在国防科研上贡献微薄之力!
文革十年,对于那时的许多人来说就是一段无法逃避的厄运。与强国强军爱国爱民背道而驰。但,领袖被架空,无产阶级专政面临被资产阶级颠覆,唯有发动群众保卫红色江山不变色;但,学生红卫兵都那么年轻,满怀美好的未来,本该在学校安静地学习知识;但,是什么原因让手无寸铁的他们,被逼到非要去造反的地步呢?
都是有血有肉的老百姓,最后却被打伤致残,有的甚至当场死亡。何苦这样惨无人道呢?!
一想到这里,我单纯的邵伟华就心痛不已。作为一名受党培养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多么希望大家能够在毛主席和党的光辉照耀下安逸地生活,而不是尔虞我诈、自相残杀。然而,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往往是不可调和的,这令邵伟华百思不得其解。
交大的红卫兵领导人得知邵伟华是带领军工厂的工人代表来校看望被打的学生,是工人阶级站出来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革命行动时,立即热情地出来迎接他们。的确,这是交大学生被打伤打残的关键时刻,工人们跑几十里路来学校看望受伤的学生,这让他们个个激动得热泪直流。学校的红卫兵们得知工人来到学校支持他们,也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把邵伟华他们围得水泄不通,拍手鼓掌表示欢迎。接下来,学校红卫兵的负责人带领他们一行人到大字报区参观了被打伤学生的实物展览。到那里一看,工人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看着一件件血衣,一张张被打伤打残的照片,邵伟华不由得想起在日本鬼子、在国民党监牢里受酷刑的革命先烈。触景生情,邵伟华又禁不住地落泪,大家也都伤心得难以言表。这场景,相信铁石心肠也会被感动的。这时候,邵伟华又十分庆幸,幸亏自己把厂党委组织打学生的行动搞散了,要不然,厂里的工人也会犯下类似大罪的。
厂党委可不是这样想的,悉数给邵伟华安上了反革命的三大罪行,并且报请市公安局逮捕法办。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雷暴雨就要倾倒了。1966年8月一到中旬,厂领导安排在厂门口搭起了开会的大台,车间的老工人同情地悄声对邵伟华说道:“厂党委说你是反革命分子,8月19日全厂开大会就要逮捕你,你没看保卫科有好几个人都在秘密的监视着你嘛?”
邵伟华一听这话,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声里透着坦然和不屑:“厂党办搭台要逮捕我?咱走着瞧,我看他们是白忙活!"
8月18日,也就是厂里搭台的第三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间新闻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公布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16条,全国上下齐震动,工厂8月19日的全厂大会要逮捕邵伟华的计划自然流产了。这真是应了邵伟华对老工人说的“让他们白忙活”的话了。
1967年7月12日,邵伟华带着专案人员小穆去四川出差进行外调工作。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手机,但信息传播特别快,15号下午他们看到成都市街道上贴着一张像流血一样的大字报,看到了自己所在的工厂里发生了武斗,死伤了很多人,有的人还认识,又看到许多无辜的工人被赶出家园,邵伟华止不住地泪流满面。大规模流血的武斗终于开始了。
要说武斗的原因,是郑州的造反派被挨打后到中央文革小组去告状,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长的江青接见告状的代表时说:“他们能打,你们为何不能文攻武卫?”从此,全国各地的武斗都称作“文攻武卫”,可怜的中国人民在无战争的情况下,两派开始互相残杀,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演变成了全国上下无情的、无人性的大残杀。
重庆市是我国武斗最凶的城市,武器最多最现代,死的人最多。其原因是蒋介石撤离大陆时潜伏了一支武装军,准备在反攻大陆时里应外合。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潜伏下来的官员随着群众组织的成立分成两派,有组织、有目的地挑起了大规模的武斗,利用文革大乱之际,到处制造杀人放火等事件。随着派性升级,两派群众组织中隐藏下来的旧军人,知道自己部队的武器库、汽车库、弹药库、医药库、军需库在什么地方,都各自操起武器、制造有组织有目的的大规模的武斗。
7月20日,邵伟华和小穆到重庆公安局搞外调,就在嘉陵江桥头,他们在现场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两辆狂奔的敝篷吉普车,上面的人站着,光着膀子,手提寒光逼人的砍刀,冲向人群,像削萝卜一样乱砍老百姓的头。一颗被砍下的人头滚落到来邵伟华他们的脚边,眼睛还在动。邵伟华吓得大叫,不知所措。小穆的胆子比邵伟华大,拉起他拼命地跑……。
跑着跑着,到了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喘息之间,看到四周的大字报都贴到了二层楼上,不知道又有什么重大新闻可看。再看那钟楼,快十二点了。邵伟华突然感到心慌,知道有事发生,就对小穆讲:“小穆,不要看大字报了,快走吧。不然公安局下班了。”小穆比邵伟华小,他很听话。当他们离开不到两分钟,四周的机枪冲锋枪步枪就响成了一片,整个解放碑大字报区就像战场一样。下午听说那里尸体堆积如山,血流成河...
文化大革命到了1968年,各单位进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宣队。在清理阶级队伍发动群众进行检举揭发时,长期隐藏在工人内部的国民党官员全部被揭发了出来。就这样,国民党隐藏下来的一个军的武装,在文革清理中全部暴露了。由于大多官兵在潜伏期没有干过坏事,有的还主动交代,就没有给他们任何处理,并且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